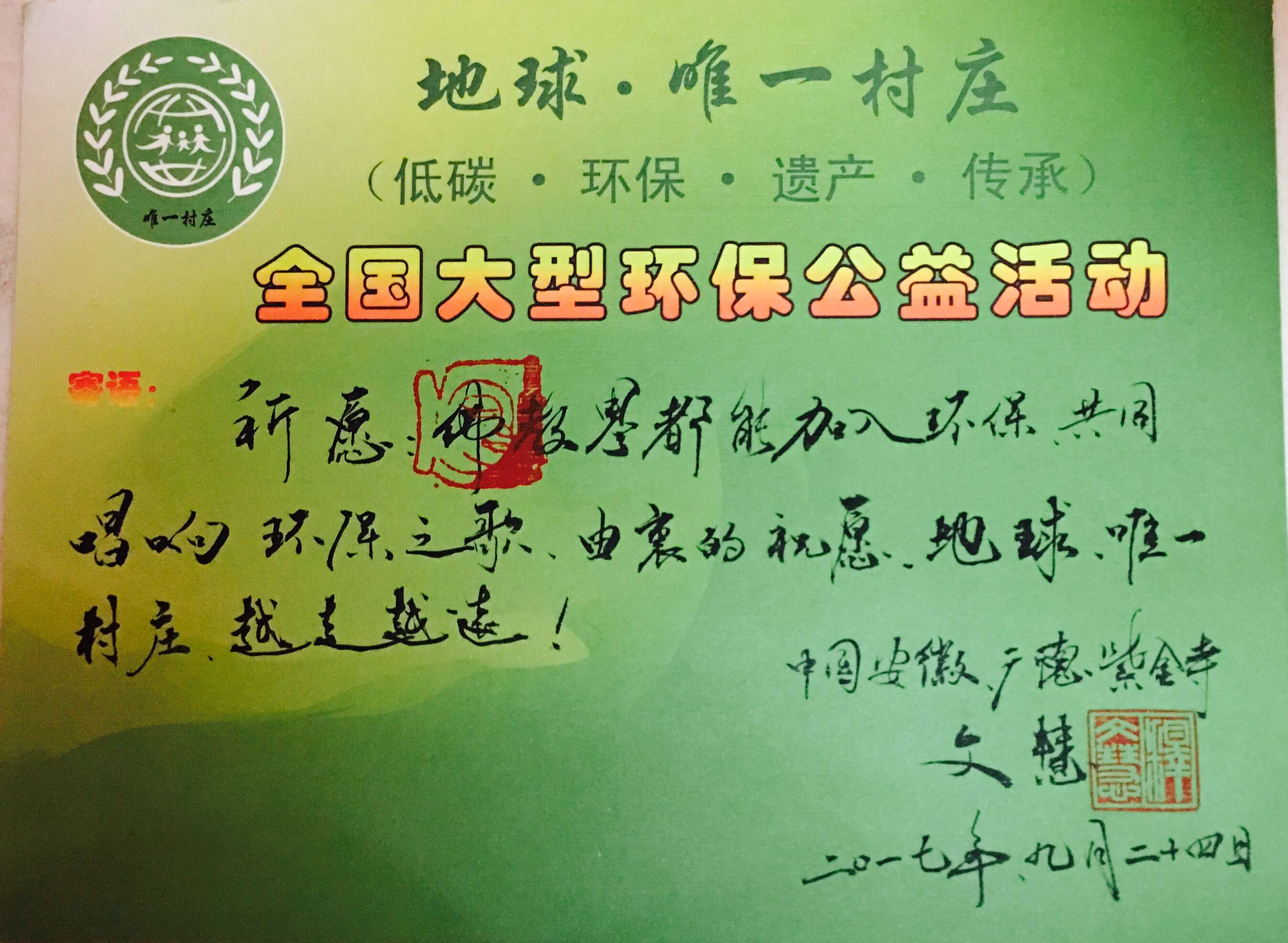专访中国林科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卢琦:“我们只治理‘人造’沙漠”
来源:腾讯网 作者: 时间:2021.07.01
腾格里沙漠是我国第四大沙漠。夏日傍晚,腾格里沙漠连绵的沙丘被日光勾勒出美丽的线条。(新华社记者 连振/图)
近几年有关沙尘暴的讨论少了很多,但2021年来,华北地区发生了4次大范围沙尘暴。沙尘暴又回来了,沙尘暴可以被根治吗?
自古以来,人与沙漠就冲突不断。远有被沙漠吞噬的西域古国,近有位于内蒙古、辽宁、吉林交界的科尔沁沙地,原本是水草肥美的大草原,现在却因过度开垦,草原沙化,成为京津风沙的主要源头之一。
为治理荒漠化,中国投入巨大,于1978年开始建设“三北防护林工程”,之后又制定《全国防沙治沙规划》。塞罕坝、库布齐、民勤、沙坡头——一个又一个治沙“典范地”走入教科书,走进人民大会堂,登上联合国的颁奖台(南方周末报道《宁夏沙坡头:沙漠不等于“沙魔”》)。
2004年以来,我国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面积连续3个监测期均保持缩减态势,终于遏制了珍贵的土地资源进一步退化。从草方格固沙到实验室测沙,治沙的科学技术不断更新。面对总体向好的治沙形势,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荒漠化研究所所长、沙漠林业实验中心主任卢琦仍保持清醒,“治沙讲究有所为,有所不为”。
接到南方周末记者电话时,卢琦正在宁夏贺兰山区域野外科考。亘古的茫茫荒漠里,他白天在荒漠中求索,夜晚与沙友谈天说地,研究者的生活也传承了几份古人的豪情,难怪他的微信昵称为“职业沙手”。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中国约170万平方公里的沙化土地中,可以治理的有约50多万平方公里,其他的100多万平方公里则是自然形成的原生沙漠,应避免人为干预。因为这些沙漠(化)的形成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我们治理的,是距今一万年以来新增的沙漠,称之为人造沙漠。”
再强调一遍,沙尘暴是个自然过程
南方周末:今春以来,沙尘暴频发。为什么沙尘暴又回来了?
卢琦:不仅从我亲身体验上,科学观测和数据也证明,北京的沙尘暴近些年是明显变少了。1990年代初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沙尘暴高发期出门一定会戴个风镜,捂着口罩,把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现在早就不用了。
今年沙尘暴看起来猛烈,但对比十年之前的沙尘暴,既算不上最强,也排不上最长,只能算偶发事例。主要是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对沙尘暴更加敏感,越敏感就越关注。
2021年春,华北多地遭遇沙尘天气。(新华社记者 李鑫/图)
南方周末:沙尘暴可以被根治吗?
卢琦:沙尘暴的持续减少说明,我们的生态建设,特别是“三北防护林”等工程措施还是有效的。但沙尘暴是个自然现象和自然过程,没有沙尘运输,我们的黄土高原是怎么形成的?
我发现公众对“沙尘暴、沙化土地、荒漠化”这几个概念分不太清楚,认为人类活动造成土地沙化,才会引发沙尘暴,所以网上甚至还有请中国去帮蒙古植树治沙的提议。但其实沙尘暴和土地沙化没有太大的因果关系,再强调一遍,沙尘暴是个自然过程。
所以不要有“根治沙尘暴”的想法,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坦然面对和处置;而治理沙漠则宜林则林、宜草则草、宜荒则荒,才是长久之道。
南方周末:除了分不清概念,公众对治沙的认识还存在什么误区?
卢琦:荒漠化有很多形式,包括风力驱动的风沙灾害、水力驱动的水土流失、化学驱动的盐渍化、温度驱动的冻融侵蚀等等。
但直到现在,公众还是把治理荒漠化简单理解为治理流沙,这是因为在西北地区流沙问题特别凸显和常见。
如果把防治荒漠化看作人,生了一场大病,那么过去的防沙治沙就是看急诊,现在病情好转要转为住院治疗,就不能只是治疗“沙”症,而是要从根本上疗伤和除根,其他几种病都要关注到,形成一套系统性的治疗方案。这就是从单一到综合的一次重大转型。最近公布的第一批十个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就是最好的佐证。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库布其沙漠,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和科学创新,治理成效显著,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新华社记者 连振/图)
今春华北频发沙尘暴,自然因素影响更大
南方周末:今春华北沙尘暴的来源,有说法认为是蒙古国过度放牧、草原沙化所致。来源问题彻底搞清了吗?
卢琦:蒙古国每平方公里才1个人,人口高度集中于大城市,所以他们的环境长期以来并没有发生天翻地覆的剧烈变化。在这次沙尘暴中,我认为自然因素还是比草原退化等人为因素重要得多。今年春季西风加强、季风减弱,加之冬春季降水少、土壤墒情差等,此消彼长使得西北刮来的一场大风,卷起沙尘暴。
这股源起蒙古国的沙尘暴可以这么类比:假设你从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开车去北京,我可以说你这车是从蒙古来的。但你开车途中要不要加油?所以吹起沙尘暴的风是来自蒙古国,但沙源地不仅是蒙古国,也有我国境内的沙漠、沙地、裸地等的一部分贡献。
南方周末:沙尘“不断上车”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们能否测算出沙尘有多少比例来自蒙古国、多大比例来自中国境内?
卢琦:现在很难测算。因为我们根本没有精准测量沙尘来源的技术手段。其一,起尘区范围和沙尘暴的经过路径很难确定。与水流的流域不同,风没有确定的边界,很难判断风吹起的是哪个区域的沙子。其二,不同沙漠的沙子在物质上差别不显著,很难通过落下来的粉尘和组分来判断它的“爸爸妈妈”是谁,是从哪座沙漠来的。这也是科学界最想突破的一个难题。
测量沙尘来源的意义在于,这是最基本的科学数据,类似治病的病理部分,掌握了数据才能有的放矢、科学决策、系统治理。
南方周末:塞罕坝、库布齐、民勤、沙坡头……这些治沙故事广为人知,中国的治沙模式经过哪些阶段?
卢琦:新中国七十余年来,治沙进程大概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全民动员、治沙造林。始于1950年代,全国上下在各地党委政府的动员下,群众固沙、造林的热情空前高涨,涌现出甘肃民勤、陕西榆林、内蒙古赤峰、河北塞罕坝这样的治沙造林典型。在河北承德塞罕坝,两代林场职工利用五十多年时间,在一片沙化土地上营造出112万亩人工林,得到了联合国颁发的“地球卫士奖”,是对这个阶段最高的褒奖。
夏日的早晨,河北省承德市境内的塞罕坝国家森林公园。(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图)
第二阶段是国家主导、工程治沙。从1978年国家批复“三北防护林”工程建设,到1991年国务院召开第一次全国防沙治沙工作会议,出台《1991-2000 年全国防沙治沙规划纲要》,防沙固沙工作纳入了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规模化治沙、造林、兴业、富民有了长足发展。
第三阶段是内外兼修、综合治沙。我国于1994年签署《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并依照公约要求,向世界治沙领先水平发起冲顶。通过各个地区的治沙实践,我们打造出了可以供不同气候区、不同荒漠化类型、不同荒漠化程度采纳的治理样板和治理模式,比如适合极端干旱区的和田模式,干旱绿洲的临泽、策勒模式,以及五位一体的铁路综合防沙治沙体系——沙坡头模式等等。这些模式已经广泛被世界各地所借鉴。
各方参与,1+1大于2,不要乱帮忙
南方周末:治沙有国家科研机构、地方政府、铁路部门、矿山等多个力量的参与,多方治沙力量如何更好地形成合力?
卢琦:过去人们的理解是,生态事业就是要由国家投资,现在看来多方参与、全民参与才是最好的安排。我认为中国的治沙模式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双向参与式”,国家出台顶层规划和设计一张蓝图,吸引全社会、全阶层、全流程参与,社会参与度反而更高。
在国家的统一规划下,各方都能拿出自己的最强项参与治沙工作,而不是乱帮忙。像企业可以出钱,科研机构可以出技术。地方政府尽职尽责治好自己范围内的荒漠化和沙化土地,铁路、矿山管好自己辖区及周边的沙化土地。当然,这些力量的集成和协调可能会产生一些衔接上的问题,就像一场接力赛,交棒往往是最难的部分。
位于库布其沙漠中的光伏发电基地。(新华社记者 连振/图)
南方周末:如何形成合力,产生1+1大于2的效果?
卢琦: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将中国的荒漠化土地分区、分类、分级,制定一揽子的治理方案,然后实行责任制,由中央和地方签署责任状,依次类推交给地方包干、区域化管控。把任务确定好后,地方交给谁来具体治理,不管是企业、社会组织还是金融部门,谁来参与都欢迎。这样就把全中国甚至全世界的力量集合到一张蓝图上。
“沙漠是资源,大漠也美丽”
南方周末:过去一些治沙项目宣传“向沙漠进军”,在你看来,防沙治沙有没有边界?
卢琦:要树立一个新理念,“沙漠是资源,大漠也美丽”。荒漠是一个独特的生态系统,能产生重要的生态服务功能。以前一般提生态系统,都指的是“山水林湖田草”,而2020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总体规划纲要》,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综合治理、系统治理、源头治理。这不仅肯定了“沙”的生态价值,并且还将“沙”首次纳入到“七位一体”的生态治理总纲,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的核心“成员”。
对荒漠的生态结构和生态功能,我们目前还只是初步的了解。所以不能武断地认为沙漠就是不好的,就要向沙漠里植树造林、改造原生沙漠。
2021年5月,在新疆吐鲁番市鄯善县,以库木塔格沙漠为主要资源的沙漠旅游逐渐升温,游客来这里欣赏连绵沙岭,感受滑沙、骑骆驼、沙漠冲浪车等项目的独特魅力。(新华社记者 丁磊/图)
南方周末:如何判断哪些原生沙漠是自然形成,是否需要治理?
卢琦:判断一片沙漠需要治理与否,一是看它的形成年代。全新世在地质学上是指大约从12000-10000年前至今的一个时期,被认为是地球开始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大的时代。我们认为,一片流沙如果形成于全新世以后,就更可能是人类活动是其形成的主导因子,当然也不能排除气候因素。在此之前的沙漠多数就是原生沙漠,这部分我们尽量不做人为干预,能保尽保。
二是看是否有重大治沙需求,诸如国家重大工程、交通运输、国防和城镇建设等,要因害设防、综合治理。综上考量,目前我国确定可治理的沙漠有五十多万平方公里,其他部分至少目前是不需要治理的部分,我们称其为“自然留白”。当然五十多万平方公里也够我们治理很长时间了。
沙漠的“可治理vs不治理”的大致范围,已经纳入我国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将严格按照生态红线管理,任何主体如果超范围地去利用规划“留白”的沙漠、沙地等地类,都会受到防沙治沙法、水土保持法等多部法律、法规的约束和限制。
南方周末:中国荒漠化治理到这个阶段,未来还有哪些难点需要突破?
卢琦:除了要重塑我们对沙漠价值的认识、制定“一揽子”的防沙治沙蓝图外,我认为中国治沙还有3个亟须要做的事情。
对一些重点区域治沙工作,我们需要专门的战略考量和统筹安排。比如黄河经过的腾格里沙漠和乌兰布和沙漠,流沙都可能直接进入黄河,加剧黄河的水沙失衡。这些沙漠与黄河接壤的节点,如沙坡头和乌兰布和刘拐子沙头,就必须得到有效控制,甚至采取非常规手段。而随着全球变暖趋势加强,青藏高原的冻融荒漠化问题也需要引起重视。目前,冻融区范围在扩展,冻融体量在增大,冻融引发的滑坡、坍塌、平地塌陷在加重,最终会导致地表沙化、退化。
针对产业化治沙,我们没有解决好社会资金的准入机制,以及进来以后怎么管理的问题。现行的“防沙治沙法”里并没有针对性的安排。比如光伏治沙,可以取得固沙和发电两方面的效益,但在具体的准入机制和管理方面尚存在争议。解决好机制问题,就能吸引更多企业参与治沙事业。
最后一个“亟”,是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治沙成就后,应该怎么走出去,为全球治沙、防治荒漠化提供中国方案。目前我国凭借“一带一路”“中非合作论坛”等国际平台的便利条件,同参与国建立防治荒漠化合作机制,定期进行防沙治沙经验交流。下一步我们应强化防治荒漠化多边合作,将我国荒漠化治理的新方法、新技术、新理念、新思路传递给各参与国,并对其国内相关工作人员进行技能培训。
南方周末记者 杨凯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