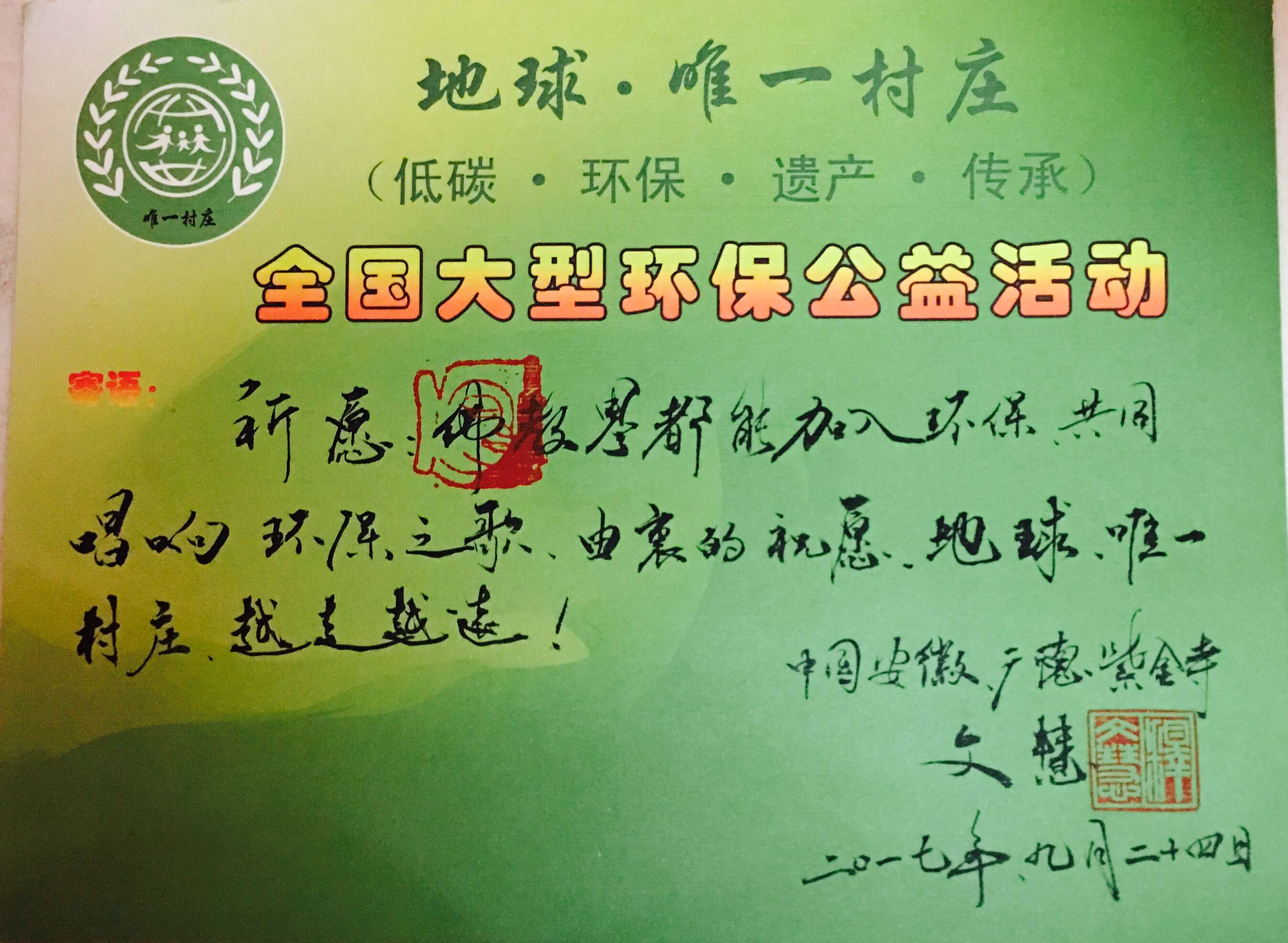郑培凯谈史景迁“另一面”:他属于美国文化艺术精英的小圈子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 时间:2022.01.05
晚年史景迁喜欢莳花弄草。他打理好家中后院的一块沼泽湿地,在旁边建起一座亭台,取名“呦呦亭”。“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典出《诗经·小雅·鹿鸣》。2019年5月,史景迁的大弟子郑培凯和妻子鄢秀去老师位于纽黑文的家中拜访,史景迁带他们探索屋后草木葳蕤的花园。正是繁花盛开的季节,花园很大,种着覆盆子等各种植物。因为园里潜藏着湿地和溪流,主人还特意让他们换上了雨靴。
一行人一直走到沼泽那边,在呦呦亭前拍照。照片上的史景迁显得有些虚弱,但仍有在园中散步和亲近自然的兴致。这是郑培凯夫妇最后一次与老师见面。呦呦亭背后深红浅粉的一树树花开得似云霞如烟火。
史景迁和郑培凯、鄢秀夫妇 图片由鄢秀提供
史景迁,一个凭天赋和本能写作的史学家,在他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几十年里,以其卓越的史学判断,独特的敏感性、同理心和优美文笔,不仅在学术研究上成绩斐然,还成功地让历史学走出象牙塔,在东西方史学界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
他师从著名的汉学家芮沃寿和芮玛丽夫妇以及《清代名人传》的作者房兆楹,中文名“史景迁”正是房兆楹所起,有“景仰司马迁”之意。史景迁并不拿自己比附那位伟大的中国史家,但其著述却无愧于司马氏所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老一辈学者如费正清等人对他赞誉有加。费正清曾评价:“在他感同身受、叙事巧妙的文字里,中国人所经历的这些,都化为有血有肉的遭遇,尽管有时候残酷不堪。通过真切摹写人物的品性及其处境,史景迁亲切地带领我们走进这些人的生命,让我们仿佛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仿佛跟他们有过直接的交流。这种感觉,只有最好的历史作品里才能赋予。”
因此,有人将史景迁与哈佛大学的孔飞力、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魏克曼并称为“三杰” 。
2014年史景迁来华时留影
当地时间2021年12月26日,这位早已须发苍苍历史学家在家中辞世,享年85岁。
消息传出,东西方学界以及史景迁的无以计数的读者,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对这位可敬学者的纪念。南都记者专访了史景迁正式招收的第一位博士研究生、著名历史学家郑培凯。他和妻子鄢秀也是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的主编。
郑培凯向南都记者回忆了史景迁的晚年时光,详述了史景迁的师承及治学特点、学术成就,厘清了钱钟书调侃史景迁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a failed novelist)的一桩公案,并且谈到史景迁不为人知的“另一面”:这位历史学家自来痴迷文学,尤其爱读当代诗。他是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与乔治·霍兰德、约翰·阿什贝利等当代著名诗人同属于美国文化艺术精英的小圈子——难怪他出口成颂,以生花妙笔倾倒众生。
南都专访郑培凯
他还有未完成的写作计划
南都:您是否了解史景迁先生在去世前的生活情况?居住在哪里,健康状况如何,是否还在写作?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住在耶鲁大学纽黑文郊外不太远的地方。居住的环境很好,房子后面有一大片园林,他种了很多花木,有的特别漂亮。在园林一侧他还种了很多覆盆子。其实覆盆子是蛮野的东西,可是他打理得很好,还可以收得覆盆子。
他很喜欢做一些园艺的事情。其实就是修剪花草啦,锄地种花啦。他家后面有一个斜坡,斜坡底端是片沼泽,他也把它打理好,甚至在沼泽隰地那边打理了一方“秘密花园”,并在园中建了一个小亭子。他做了很多在我们看来像农活一样的事。
史景迁与郑培凯 图片由鄢秀提供
他生前还蛮喜欢劳动的。只是他的健康状况在三四年前开始不太好了,得了慢性病,身体协调出了点问题。这造成他后来动作越来越慢,园艺的活也不太能做了。平时就散散步。他过世前两个星期摔了一跤,导致他身体慢慢地越来越弱,最后过世了。
他晚年读书,特别喜欢读文学的东西,读读诗,读小说等等。他最后也还是有一个写作的计划,这个计划没有完成,因为身体太弱了。他想要讨论西方思想当中,涉及中国儒家思想的材料,特别是孔子的《论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资料大体整理好了,可惜没有写完。
他的传道授业是很开放式的
南都:您是史景迁收的第一个博士生,能否透露史景迁先生是一个怎样的导师?他以什么方式带徒弟,如何传道授业解惑?
郑培凯:史景迁先生非常地照顾学生。他有一个特别的能力,通过跟学生谈话和交往,可以了解到这个学生的性格和做学问的倾向。他基本上是让学生发展自己,从来没有要求学生,要跟着老师的路子做下去,发扬光大我的学术体系,成立家派。他其实是不赞成什么学术体系与家派的。
所以我们看到史景迁先生带出很多很优秀的学生,这些学生每个人都有独立发展的学术方向。史景迁没什么家派观念的,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希望每个人自由发展,每个人最充分地发展自己的所能。每个人能力不一样,兴趣不一样,追求也不完全相同。但只要是在学术范围的发展,他都特别鼓励。
至于他如何传道授业解惑,如上所说,他传道的方式是比较开放性的。他的授业呢,他会仔细地看你写的东西。因为英文不是我的母语,虽然写得通,但文采会有问题,而且有的时候表达不是按照英语的思维逻辑。他会帮我改文章,改得还蛮仔细。他自己的文字非常优美,所以他帮我改也改得很好。
在花园散步的史景迁与郑培凯 图片由鄢秀提供
至于解惑方面,他的方法很有意思,比较开放。就是说,你已经读博士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应该有的。你发现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你应该自己去找,老师不能去帮你找答案。你找到的答案,他帮你看看,某个地方还应该更清楚一点,你就再去找一点资料。假如资料已经穷尽,那你就要设法把它讲清楚,能够讲几分就讲几分。
南都:史景迁是芮玛丽的学生,芮玛丽又是汉学家、历史学家费正清教授的弟子,您能不能梳理一下从费正清到芮玛丽、史景迁,再到您这一代的学术传承?
郑培凯:史景迁的老师是芮玛丽。芮玛丽的先生是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Arthur Wright自己不太用芮沃寿这个名字。芮玛丽、芮沃寿夫妇都是教史景迁的,主要是芮玛丽。
芮玛丽是费正清的大弟子。她跟列文森、费维恺都是费正清的学生。芮玛丽后来嫁给Arthur Wright,他们两个人原先在斯坦福,后来夫妻俩一起到了耶鲁,做了耶鲁的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的教授。
Arthur Wright倒不是费正清的学生,他的辈分相当于费正清的师弟,也是哈佛出身。他本来是研究欧洲思想的,他的硕士论文做的是布鲁诺,16世纪欧洲的一个比较叛逆的异端思想家,研究当时的思想环境。Arthur Wright后来转向研究佛教史,他对中国的佛教思想很有兴趣。后来又转为研究儒家思想,推动西方学界的儒家研究。
所以呢,的确史景迁的两个老师都是哈佛出身的。芮玛丽是费正清的学生,Arthur Wright算费正清的师弟。史景迁从芮玛丽这里受到比较多学术训练,可是有一点很重要,他在做论文的时候,两位老师给他介绍了房兆楹,史景迁跟了房兆楹一段时间。房兆楹在传统中国史学,特别是明清史方面,功底比较深厚,Arthur Wright的影响主要是有朋友介绍给他。
史景迁家中悬挂的张充和书法
Arthur Wright和房兆楹跟胡适这一代关系比较密切,所以也跟中央研究院和故宫的一批人有一定的联系。这就使得史景迁在做博士论文《康熙与曹寅》的时候,可以到台北的故宫去找资料。那时候台北故宫的档案,特别是宫中档并没有开放给学者研究。所以史景迁得天独厚,他可以参考台湾故宫(当时还在台中)的康熙御批文档,这对他的学术成就,提供了关键性的贡献。
我是史景迁正式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我的研究方向是16世纪中西最早的接触以及早期全球化雏形出现的历史。史景迁觉得我的题目和他并不相同,因为他是研究清朝及以后的。所以他在指导我的时候,Arthur Wright也同时指导了我在古代史这方面的研究。但Arthur Wright过世很早,我还没写论文,Arthur Wright突然因为心脏病过世了。他走了,历史系就空出一个讲座教授的位子。史景迁很厉害,他说服了学校,由他出面去请哈佛的余英时,把余英时挖角挖过来,做我的论文评审。耶鲁因此聘了余英时做讲座教授,我也就有了两个老师,史景迁是主要的论文指导,余英时是评审论文的老师。其实我跟他们两个都很熟,来往很多,受益也非常多。这是我的师承。其他的我的师弟师妹,当然都是出自史景迁门下。
他是金针度人,工夫花在背后
南都:史景迁是历史学家里的“讲故事的人”,他的文笔生动细腻、充满细节和想象,富于文学性。对于这一点,学界有人认为他“不够学术”,钱钟书戏称他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您个人怎么评价史景迁的这种治学方式和修辞策略?
郑培凯:关于这个问题,有些是传闻,有些是断章取义,然后以讹传讹。其实,历史写作文笔生动,故事叙述的精彩,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的人可能为了掩饰自己没有史景迁高超的表达能力,可是自己觉得学问也不错,怎么没能享大名,总是想要暗示他的学术根底不好。这是很奇怪的一种态度,而且大多数都是中国学者。可能是嫉妒吧。中国人现在有一个新的名词,羡慕嫉妒恨。
现在有的年轻的学者用这样的态度批评老辈学者,是很轻佻鲁莽的。他们还会引用一些权威人物说过的话,随便给人定性。钱钟书先生这个人讲话,偶尔尖酸刻薄,我们都知道,他是极度聪明,有时管不住嘴。他假如捧你,经常是不把你放在眼里,随便说说;假如他批评你或者讽刺你,反而表示看得起你,可是也能看到你的缺欠。人无完人,他批评的大都是古人,也总是有某些可以批评之处。你有没有发现,钱钟书从来不批评比他差的人,或者是后辈,钱钟书从来不批评后辈。
钱钟书先生
所以就出现了很有趣的现象。钱钟书觉得,史景迁写历史这种写法,干脆写小说算了嘛,但他又不会写小说,是一个“不成功的小说家”。所谓的failed novelist,failed不要翻译成“失败的”,英文也不是那么简单直白的意思。Failed在这里的意思是不成功的,一个没有成为小说家的人。比方说我们要演出一个剧,已经安排献演了,但又没演成,这就是一个failed play。大家引述钱先生,讲史景迁是一个“失败的小说家”,翻译首先就误会了,没听懂弦外之音。
许多年轻的学者,自己的中英文根底都不好,他一看到这个硬译过来的词,就误会了。其实钱先生说这句话不见得是有意讽刺,可能是说个笑话,显示自己的俏皮。钱先生的嘴是关不住的,大概比他长一辈的,都被他讥讽过,古人也被他讽刺过,可是我们晓得他还蛮尊重史景迁的。他讲的俏皮笑话,也只有他有资格讲,现在的后辈千万不要当真,画虎不成反类犬,弄巧成拙,就成了轻佻的“洋场恶少”了。我们当时听了,也就笑笑,觉得很好玩。
至于史景迁叙述一个故事,为什么叙述得这么动听呢?首先是他很会找资料。经常是中文资料、原文文献他找过了,可这个文献不足以铺垫出一个很清楚的历史图像,所以再去找各种各样相关的历史材料,把这个时空的所有的历史环境搞清楚。人间处境他呈现了,然后把他最先掌握的有关人物的历史材料放进去,把它捋清,这就是一个故事。
我们看他研究的方式,通常一开始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题目,主题很清楚。然后,他找各种各样的资料,把这个主题在历史里展现出来。他不会说找到这个文献,就死钻这个文献,考证与对勘不同的材料,是甲说的这个部分对呢,还是乙说的部分对呢,还是有一些问题呢,他不是这种考据型的学术研究。
从史景迁的历史写作我们看出,他有一个宏观的历史认识。他原来做清初,后来延伸到晚明。从晚明以来,整个中国历史发展大的环境、氛围跟历史走向是怎么回事,这个他有兴趣。这是宏观的。因为他教近现代史,在耶鲁教了几十年,他必须要从16世纪讲到20世纪,永远在思考这些问题。
有了宏观的整体架构,再做一个很细的、看起来很小的题目。比如他主要通过人物写历史,可是把人物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的时候,你必须把人物和环境的关系讲清楚。这就是史景迁的本领。宏观的观照跟微观的细部呈现相结合,你读起来会觉得,有先有后,顺序清楚,历史的图像也就徐徐展开了。这哪里不是学术?这当然是学术。
其实讲起来也蛮有意思。有的人居然说钱钟书研究的东西支离破碎,完全没有系统,不是学术。钱钟书哪里没有系统?钱钟书对于中西文学背后的文化背景,宏观的方面他是了然于心的。他就是一步一步写一些读书札记,这些札记每一个都是研究题目,都可以铺展成一本专著。钱先生有一个有趣的地方,也是极为傲气的地方,他谈学问,一般点到为止,因为他是讲给上乗人的,懂的人自然知道,你学问没有到这个地步,你门墙都还没进,怎么有资格去看百官之富、宫室之美?
所以呢,钱先生的方法是不把金针度给人。你达不到这个程度,根本没资格看我的东西。你没资格看,还要叽叽咕咕讲,那么我就一笑置之。史景迁是另外一种,他就是金针度人,他把一切都弄好了给你看。可是你不知道他背后花了多少工夫。他背后的材料,背后的整理,背后的组织,以及他写作的时候,聚精会神把一个故事,一个历史的现象,一个历史人物经过的历史阶段,他的生平或者生命中一个特别的片段,把它突出展现。这是史景迁呈现历史的方式。
他属于美国精英文化艺术的小圈子
南都:之前您在一个访谈里提到,史景迁是文史哲打通的,不像现代学科分化之后,中国学者只有囿于自己的一小块天地。据说他还喜欢阅读文学作品,尤其是诗歌。据您所知,他日常有怎样的阅读习惯?他喜欢读哪些作家的作品?
郑培凯:其实古代的学者大多都是文史哲打通的。现在因为学术分化,专业化、职场化,人文的跟科学的、理工的、医学的,甚至社会科学的,越分越细以后,就出现了断裂,甚至出现了某些奇葩,学历史的不看文学作品,学文学的不参考历史著作,学哲学的什么都不看,真是二十一世纪怪现象。大多数人进入学术界,学术界对他们有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很简单,就是你是个专家。别的不懂没关系,反正大学里有别人懂别的。
有的人是寻求自己的知识,即孔子所谓的“为己之学”。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里,学术变成一个职业,这是一个职场,它有要求,学术变成了“为人之学”。可是我们看比较了不起的学者,像钱钟书、余英时、史景迁……这些人还是在追求自己的兴趣。他这一生的学术追求,其实就是他对知识的追求。对知识的追求就没有文、史、哲那么清楚的分界,因为它都是通的,是连在一起的。
史景迁很喜欢文学作品。所以钱钟书有点笑话他,说他应该搞文学,不应该搞历史,说他是个“不成功的小说家”。史景迁最喜欢的却是诗。他从小浸淫于古典文学,从古希腊罗马文学到莎士比亚。他读英文小说,也读整个欧陆的小说。诗歌方面他读古典诗,也经常读当代的诗。
有两个诗人他时常跟我讨论。我自己也写诗,虽然不怎么发表,可是我喜欢诗。他有时候跟我讨论,一个是约翰·霍兰德(John Hollander)。霍兰德是美国东部的一个诗人,后来也做了耶鲁的讲座教授。他的诗蛮有意思,他对音韵之美很讲究。英诗的韵律传统上很规整,现在比较自由,可自由当中也有一定的韵律。霍兰德的诗除了意象很鲜明,音韵方面的强调也很独特,这很值得我们想想,史景迁写作,在遣词用字上,也讲究文字的节奏与韵律。
约翰·霍兰德成名于1958年,耶鲁大学给他出了一本诗集,隶属于“耶鲁青年诗人系列”,编者是了不起的英国大诗人W.H.奥登。史景迁跟霍兰德有比较多的来往,而且他们都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所以他们也算是“同行”。所谓同行,不是说他们是教书的同行,而是他们都属于麦克·阿瑟天才奖那一类。
美国著名当代诗人约翰·阿什贝利
还有一个诗人是史景迁很喜欢的,约翰·阿什贝利(John Ashbery)。约翰·阿什贝利在美国诗坛影响很大。我记得有一次史景迁拿给我看他最近得到的一本新的阿什贝利的诗集。阿什贝利也得过麦克·阿瑟天才奖。
换句话说,史景迁喜欢诗,当然也跟他认得的这些诗人有关,可最主要的是,他在这个圈子里。他自己不写诗,但他属于美国文化艺术精英这个小圈子。这个小圈子里的人得的奖也很特别,MacArthur Fellows Program or MacArthur Fellowship,中文翻译过来叫麦克·阿瑟天才奖。它给你一大笔奖金,有时候三年,有些是五年,随你做什么,也不过问。只要觉得你是一个不得了的、可以变成大师的人,就给你这一笔钱,那你就不必担心生活,学校当然也高兴得不得了。这种民间的基金,是有助于文化发展的。
他开启了西方史学研究的许多新面相
南都:《王氏之死》是史景迁在《康熙》之后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他自己非常看重的一部作品。史景迁为什么对山东郯城的一个农妇的命运感兴趣?这种对历史当中卑微的小人物关注、同情,以及通过小人物来反映社会历史图景,这在当时的学术界具有什么意义?
郑培凯:其实蛮有意思。这是一个命案。当时做法律的参考书《刑案汇览》里面记载了这个案子。有前有后,有简单的故事轮廓。就好像我们今天发生了一个命案,从头到尾记录下来。可是还有一本《福惠全书》,是给那些太守、县令的师爷们作参考用的,也记载了这个案子。所以不是一个孤立的材料。
发现这一点后,史景迁就开始去把山东郯城的地方志找来看。蒲松龄也在那一带活动过。这几个连起来,就勾勒出了地方的整个环境、经济、社会,以及清朝在这个地方社会里的结构。通过这个命案,可以显示出地方行政的运作。山东郯城算是比较偏僻的,怎么执行大清帝国中央的政令呢?原先史景迁研究的是康熙皇帝,这个案件发生在地方上,人物是一个贫民农妇王氏,怎么具体地展现地方上,以小见大的历史状况呢?
《王氏之死》是很有趣的一本书,也是史景迁自己蛮喜欢的一本书。它能够把这些东西编织起来,组织这些材料,然后从不同层面思考,清朝小地方的人,生活在大中国的环境中,她的处境是怎样的?她可能有什么遭遇?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段落,是王氏在雪地里做梦的那一段,那是蒲松龄的材料,应该是蒲松龄的梦,移置到王氏身上,像是扶鸾之后仙魔附体了。这也在清代郯城这个小地方,做梦想像的可能性,意识或者下意识活动的可能性,材料来自蒲松龄,这种探索是非常有趣,很吸引人的。
《王氏之死》在西方好评如潮,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主要是启发了我们,历史怎么写?你想要反映什么历史的环境?你问王氏死前昏迷了做梦,是否会梦见这些东西?天知道。可是有没有人可以想象这些东西呢?在当时山东这个小地方,有,蒲松林就这么想。史景迁扩展了整个历史想象的空间,基础却还是历史的材料。你要注意到,所有材料他都在注解里列出来了。所以,他在西方史学的研究上,开启了许多新的面向。这也是为什么史景迁在史学界影响这么大。
史景迁与妻子金安平 2014年来华留影 理想国供图
南都:在美国研究中国历史,有哪些利与弊?
郑培凯:我们知道,每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学术环境,用不同的语言来表达学术,环境是不一样的。在美国,开放性很大,启发人思考的空间很大。中国的历史界,我觉得比较封闭,又比较传统,条条框框太多。在中国的文史界,所谓的封闭和传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
一方面有从司马迁讲起,两三千年的史学传统的影响,可是另一方面,五四运动以后,新学制出现、新的教育体系出现、新的学术思想出现,我们学西方、学实证,甚至饥不择食地学些半生不熟的新理论。有时候我感到很遗憾,中国有深厚的传统,又能够向西方学,怎么都学的都是一些封闭性的东西?是一种表面很严谨的封闭性。这个不是很好的。
我们当然知道清朝考据学有实证精神,可是在故纸堆中研求文献实证,是会限制人的思考。我们从西方学史学方法,也学他们的实证精神,那是很好的,可以破除迷信,破除中国民间文化里封闭迷信的思想。可是出现了另外一个问题,你要是只按照实证来做文史研究,就难免落入考据的窠臼,你就不能放开来想象。摒除了海阔天空的想像空间,没有鸢飞鱼跃的环境,就很麻烦了。所以我们时常看到中国的学者很拘谨,想事情的方法比较固蔽一点。
他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一种深层的求知欲
南都:您觉得史景迁为什么着迷于研究中国历史?
郑培凯:其实他原来也不是研究中国史的,他是到了耶鲁以后才开始接触中国史。可是他跟我讲了他童年的一个故事。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他父母带他去看一个展览,展览里有一些中国的文物,比如玉器、青铜器、书画之类。他觉得这个世界好特别啊,他很沉迷中国文化里一些奥秘的东西,他搞不懂。他当然没有机会再去钻研,那时候他那么小。可这个东西深深藏在他的心里。后来他已经变成了重要的中国历史学者,他跟我讲,不晓得是不是藏在他心底的,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是艺术品所展现的那种奥秘感,那种奇妙的,有一点捉摸不定的,搞不清楚的东西,促使他要去探索。所以这是一种深层的求知欲望。
其实很难讲,童年的一些挥之不去的向往、迷恋,到底会影响我们人生多少呢?你问我,我也没办法告诉你,史景迁下决定这辈子研究中国史的那一刻,关键的因素是什么。可他后来告诉我这个故事很好玩,一直在他心里头,萦绕在那里,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他对西方了解中国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南都:担任理想国·史景迁作品系列的主编,您认为这套书是否忠实地呈现了史景迁的文风特色?史景迁的作品为什么能受到东西方读者的喜爱?
郑培凯:我主编的这套史景迁的著作集,大体上是忠实地反映了史景迁著作的面貌。可是翻译是很难的一件事,尤其史景迁的文笔是这么的优美,这就有一点翻译上的困难。我想有一些人已经开始在讨论不同译本的差异与优劣。不同的译者,在读原文的时候理解有所不同,落笔翻译的展现方式又不太一样。我们选择的译本,是大体上意思到了,是不是完全展示了原文的韵味,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他整个的历史叙述,在结构上,在题材上,译文都还有比较忠实的再现。我们在处理译文的时候有没有困难?也有的。因为所有的译本,我们都发现,在原文的理解上有个别的小差错。因为史景迁表达一个历史场景也好,人物的心理也好,有的时候遣词用字是比较婉转,比较曲折的。婉转曲折的英文表达,虽然看起来很流畅细腻,这种文章却最难翻译。所以我们在处理译者的译本的时候,时常发现误读。都是很小的错误,大意不失,但味道就不对了。这时候,我们做主编,除了更正翻译的具体小错误,不会改动其他的东西。
也有个情况,是史景迁原文里头,反映了他在理解中文原文文献的时候出现误读,这个我们不改,这是史景迁的问题。我们只管翻译,只管把著作译介出来。我作为他的学生,我也不会写一篇文章去批评老师,不会去吹毛求疵。
至于史景迁的历史著作为什么会赢得那么多读者喜爱,因为他文笔好,叙事清楚,他讲的所有历史情况都是有学术文献支持的。他的著作,你看后面的注解,无一字无来历,可他把它编织得很好。读下来,引人入胜。
所以,我觉得史景迁对西方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不讨论当前的一些政治冲突,也不会从哪个利益角度,比如国家利益角度,来探讨历史文化上的问题。这就能够丰富我们对人类文明的理解。而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南都记者 黄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