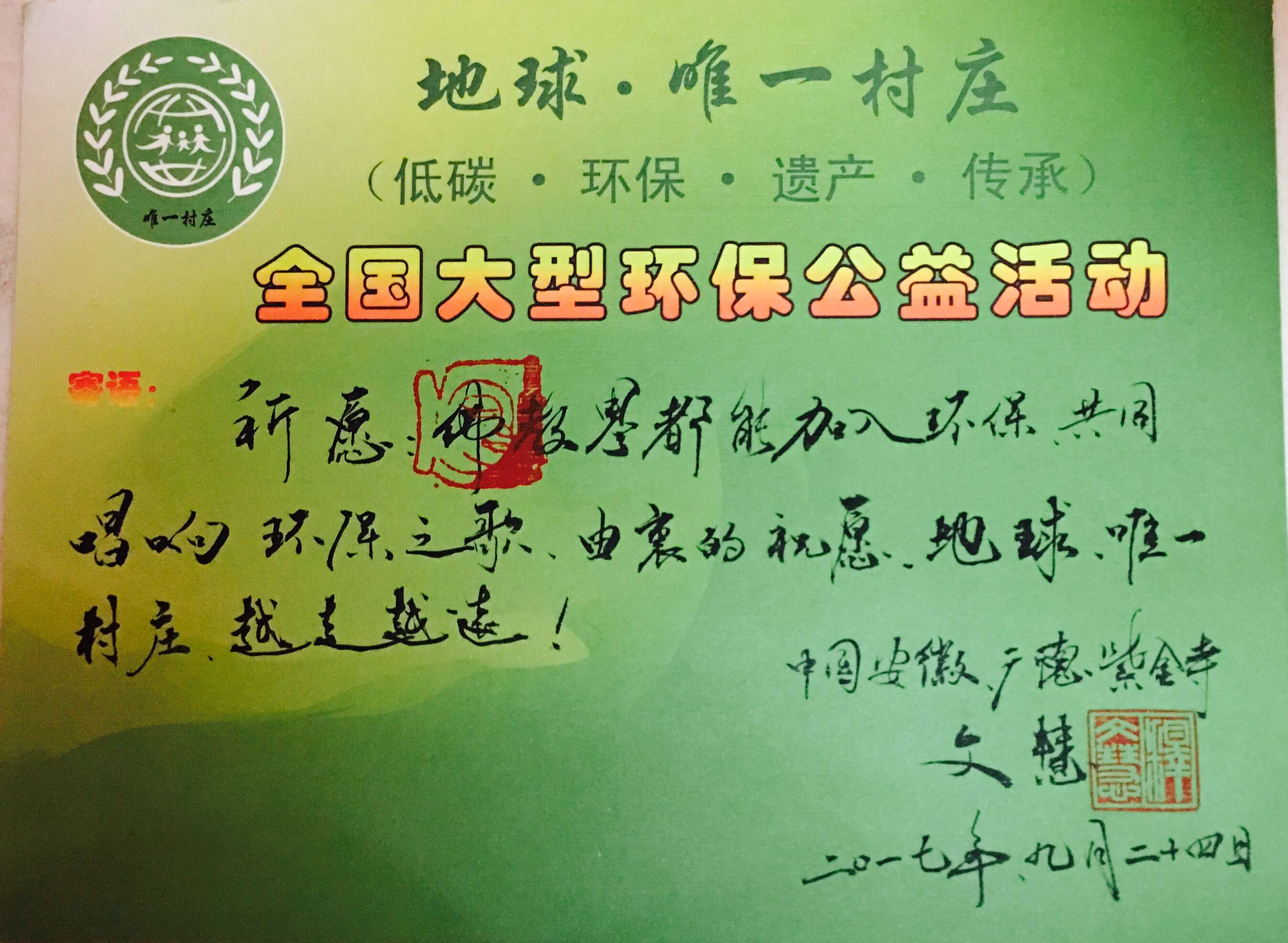李娟:阿勒泰的精灵歌
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 时间:2012.07.24

李娟的许多文字都是伴着缝纫机写出来的

李娟的生活与这些赶场的牛羊紧紧相连

与动物亲密接触好快乐
走过高悬在蓝色额尔齐斯河上空摇摇摆摆的吊桥,她说:“烦死了,怎么这么蓝。”
听着冬不拉,在深远、寂寞的深山里的集会上,她说:“牧人们所领略的快乐与这片大地上那些久远时间中曾有过的快乐似乎没有什么不同。”
有人随意地躺在草原上、岩石边、树阴里,她说:“那样的睡眠是不会有梦的,只是睡,只是睡……”
喀纳斯、巴尔拉茨、可可托海、沙依横布拉克……这里有阿勒泰地区迥然的原始美丽。在这片一两步便是天堂的土地上,一个个向往又敬仰的脚步,走了又来,来了又走。可是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样的文字。在梁文道眼中,李娟是那年他最大的发现。《阿勒泰的角落》一书中的第一篇就已经让他觉得李娟“惊为天人”。
其实,李娟只是个瘦小、留着短发、戴着眼镜的普通女孩。她当裁缝,卖着小百货,和家人一起,跟着哈萨克族的牧人们随着季节的交替迁徙在阿勒泰的草原与森林之间。这样一个普通女生的文字却给作家刘亮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为读到这样的散文感到幸福,因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已经很难写出这种东西了。那些会写文章的人,几乎用全部的人生去学做文章了,不大知道生活是怎么回事。而潜心生活,深有感悟的人们又不会或不屑于文字。文学就这样一百年一百年地与真实背道而驰。只有像李娟这样不是作家的山野女孩,做着裁缝、卖着小百货,怀着对生存本能的感激与新奇,一个人面对整个的山野草原,写出不一样的天才般的鲜活文字。”
对此,李娟有自己的回应:“那时的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都挥之不去,便慢慢写了出来。如果说其中也有几篇漂亮的文字,那倒不是我写得有多好,而是出于我所描述的对象自身的美好。”
不管怎样,既然别人写不出李娟般的文字,而又非要用什么词语或句子形容她和她的文字不可,那么就当这是精灵在歌唱吧。
走墨笔尖的天堂
有人问我,李娟都写了什么?
我说,母亲、外婆、邻居孩子、小狗、小猫、小白兔,还有山川河流,绿树草原……
有人说,她写的是浪漫,是无边的寂寞。
我说,是生活。
李娟的书里,每篇文字都有着自己的故事,彼此看起来相互独立着。但只要细细读完整本书,你会发现眼前就是一幅完整的阿勒泰拼图。这里有最原始的土地,最老实的牧人,最古老的毡房,还有李娟最初的回忆,或多或少,或喜或悲。“但老实说,其中也不乏天真可亲的片断,令现在的自己都羡慕不已”。
有关一个普通人。
李娟家在阿勒泰牧区,经营着一家半流动的杂货店兼裁缝店。店里有一个账本。当地的牧人们在店里赊了账,都会在上面签个名,留作凭证。等结清了账,再把名字划去。“在喀吾图,一个浅浅写在薄纸上的名字就能紧紧缚住一个人。”因为在这里,“牧民们都老实巴交的,又有信仰,一般不会赖账。”对,这只是一般情况。有个名字已经赖了几年,直到账本上的名字都划去的时候,它还在那儿。这个名字很复杂,又是阿拉伯文,作为当地仅有的几个汉族人,李娟她们基本上都快忘记这个人了,就连他长什么样都不记得了。虽然他欠了李娟家八十块钱,可她们实在不知道他是谁。
八十块钱对于李娟这样在牧区做着小营生的家庭不是一笔小钱。他们开始在附近托邻里熟人打听起来。中国有句古话叫做“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虽然用在这里不怎么妥当,可那个人确实在冬天里的某一天又来到了李娟家的小店。她们拿出账本请他辨认。他看了之后大吃一惊:“这个,这个,不是我吗?这是我的名字呀!这是我写的字啊。”他已经记不得是否赊过账了。他很抱歉:“实在想不起来了……”
当晚,他送来了二十元钱。又在接下来的八个月里,分四次还完了剩下的六十。李娟觉得,“看来他真的很穷。”
借债、还钱、赊账,这种市侩琐事在这里被打上了真善美的痕迹。对于李娟来说,只要在阿勒泰,就算是补鞋这样“又臭又丢人”的活儿,都能在她的记忆里找到一个幸福的角落。
李娟的叔叔拿着李娟妈妈补鞋的全套工具开起了补鞋店。
李妈妈进了城,看见市场里补鞋的生意不错,便跑到乌鲁木齐添置了一全套补鞋的工具。可她既不愿学手艺,还嫌人家脚臭,这工具就一直闲着。“还是我叔叔厉害,他不怕臭。”李叔叔半路出家,无师自通,拾起了这套家什。先拿家里人做完实验,李叔叔就开张了。
“可怜的喀吾图老乡们不明真相,看他头发那么白,以为是老师傅,信任得不得了。”不过呢,好在村子小,人情浓,补得不好,大家照样付钱穿走,大不了回家再去修补。手艺不佳不要紧,一点都不妨碍李叔叔生意的兴隆,甚至出现过排队加塞的情况。
“我叔叔刚放下锥子去拿剪刀的那会儿功夫,‘啪’地把鞋子递过来要你抽空钉个钉子。等他放下剪刀去拿锥子时,又被要求再给钉一个钉子。于是我叔叔就晕头转向地给这个钉一下,再给那个敲一敲。弄来弄去连自己原先正修着的那一双该修哪了都给忘记了。最后干脆是放到哪儿了都不知道了(大概又被哪个好心人给藏起来了)。鞋主人简直快吐血了,一边求爷爷告奶奶满房子翻找,一边跑出去看车,再大声喊一声:‘再等一等,最后十分钟。’。”
旁边的人则铆足劲齐声大喊:“快点,快点,快点——”
看着李叔叔这样的“瞎忙活”,李妈妈便开始畅想:骑自行车周游全国;在城里买套房子,像海报上那样装修;老了要养猫养狗逛街;住每年都能去海滨疗养一次的那种养老院……美滋滋地想了老半天,李妈妈就会把脸扭过来对正为补鞋子忙得不可开交的叔叔说:“好好努力吧!为了这个目标……”
补鞋子确实赚不了大钱,更何况是李叔叔这样的“笨蛋”。但李娟“喜欢并依赖这样的生活,有希望的,能够总是发现乐趣的生活”。李妈妈也说:“补鞋子那一套家什谁也不给,就给娟儿留着。”
文字是心灵的延伸。在李娟的心里,“小九九”太多了,于是化作文字,生长在白净的纸上,成了她的延伸。而她又切切实实地生活在周围这个名叫阿勒泰的世界里。这就是她的生活。她所记录的就是这些。当然,还远不止这些。
杂货店的无本行当
最初的写作是在小学二年级,李娟开始给远方的母亲写信。她觉得写点什么是件愉快的事情。“作文语言比较机智,总是得到老师的表扬”,李娟回忆道。不过事实是,老师的表扬有点“过火”。也是在二年级,李娟写了一篇关于雪的三百字小作文。她忘不了那个“过火”的老师,郑老师。一开始,事情进展得都很顺利,郑老师当着全班朗读了李娟的作文。可后来,郑老师的“无理要求”点燃了一部分男生心中的怒火——背诵,否则不放学。那些不服气的淘气小男生怎么受得了这种“憋屈”。虽然在老师面前他们都乖模乖样地背了,可在暗地里却不会轻易屈服,在李娟回家的路上,男生们“埋伏”了李娟,上演了一出“校园暴力事件”。
有很多人说李娟是天才。所谓天才,不就天生是写作的人才么?李娟不同意:“我不是天才。如果我还是个十七八岁,二十出头的小姑娘,倒还可以担当一番‘天才’这个名头。但毕竟三十多岁的人了……我也并不是一开始就写成这样的,我的写作有其漫长而明显的进步过程。”说起写作,李娟确实经历了从偷偷摸摸到光明正大的过程。十多年前,李娟的文章全是背着母亲写出来的。她不想让母亲知道她正记录下她们的生活给别人看,更不想周围的人知道。她说:“一旦他们知道了,就会把我看成跟他们不一样的人,我就不能再贴近他们。”
这些“地下文字”的载体是一些大大小小的纸壳纸片。作家刘亮程回忆:李娟的散文一片片从阿勒泰山区寄来,大多写在一些不规则的纸片上,字也细小拥挤,但不妨碍文字的耀眼光芒。最早开始写的时候,因为想省纸,李娟就两行并做一行地写在日记本上,然后撕下来去投稿。后来,这些纸片成了《九篇雪》。几年之后,李娟开始光明正大地写了。因为“谁也没见过我的书,只见过我趿着拖鞋一脸煤灰地满村子赶鸭子”。
关于写作,李娟这样说:“我从小就想确定一生的理想。我喜欢画画,但是发现画画太浪费钱了。只有写作不要本钱!其他啥都要投资,投资!”于是,李娟在自家的杂货店里做起了这份“无本行当”。
由于户口原因,再加上家里经济条件所限,李娟从富蕴县二中退了学。十七八岁的年纪,她开始跟着母亲学做裁缝,之后又只身一人去乌鲁木齐打工。在乌鲁木齐,她做过地下服装厂流水线的裁缝工、超市售货员、声讯台的传呼小姐……这里的工作有种说不出来的苦。有一段时间,李娟最大的愿望就是跟一个可以帮她买秋衣秋裤的老板干活,而不是守着每月才250块钱的工资。想起那段日子,她说:“我真是个二百五。”
打工是打不下去了,做裁缝也没什么出路,怎么办?李娟没有忘记曾做过的投资:写作。她开始投稿,机会纷至沓来。很快,她出书了。“早知如此……”
《丝路游》杂志的段离在2001年意外地发现了李娟的《马桩子》。这一年,李娟二十出头。段离把李娟请到杂志社当编辑,她说:“当年的李娟像一个受惊的鼹鼠,黑豆般的眼睛,藏在用胶布裹着的断了腿的近视眼镜后面,滴溜溜地转着。”随后,发现李娟这块“大宝贝”的人越来越多,她的“阿勒泰”靠着口口相传被更多人所认识。
在2010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十大好书”评选中,很多人看好她。评委们却不这样认为:写作太过个人化,显得过于轻浅,格局也不开阔。接下来的2011华语传媒大奖上,她被提名“新人奖”。依然是没获奖。可事实是,李娟的文字是不需要奖项证明的,她也无意闯入这世俗功利的凡尘游戏。或许有在“羊道”,“冬窝子”这些地方,她更能放声歌唱。
安静地漂泊流浪
瘦弱的李娟似乎天生就适合被母亲拖着流浪。
“我5岁的时候,体重只有十一公斤半,都上了三年级了,还在穿四岁小孩的童鞋。”
李妈妈可能觉得李娟小得还不够,说:“你要是永远都那么小就好了。从来不让人操心。上火车只需轻轻一拎,想去哪儿去哪儿,根本意识不到身边还带着个人。整天也不说话,给个小凳就可以坐半天一动不动。困了倒头就睡,睡醒了继续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李娟的老家在四川乐至县。幼时的李娟和外婆还有老外婆(李娟外婆的母亲)生活在南街的一个天井里。那时候,李妈妈独自在外做营生,有时也会回家,拎着李娟一块去行走他乡,然后又把她送回来。
直到,李娟十三岁,她和八十一岁的外婆送走了一百零七岁的老外婆……后来,十七八岁的李娟远离家乡,去往了新疆的富蕴县。
在遥远的哈萨克牧区,每到开春解冻,哈萨克人就离开他们的冬宿地,牵着马、牛、羊,赶往新绿的春牧场;夏天到了,他们又跟着绿草迁到高地;当秋天的风扫过一片金黄时,他们便转移到了河谷,追着那片快要消失的绿;等到萧瑟的冬天,他们会再一次回到一年前的那个冬牧场。李娟家的杂货店做的就是这些牧民的生意,他们跟着羊群赶场,从冬牧场到夏牧场,从南方又回到北方。在哈族地区做生意,语言是第一道坎。
“我妈仗着自己聪明,在汉语和哈萨克语之间胡乱翻译,还创造出了无数新词汇,极大地误导了当地人民对汉语的理解。”“小鸟”牌香烟就是李妈妈的专利。
有个哈族小伙去店里买烟,说要“小鸟”牌。他用的还是极其标准的普通话。在看完柜台上所有的香烟之后,李娟说:“我们没有‘小鸟’烟。”小伙指了指,说:“有的!那里那里!”“什么啊!那是相思鸟。”因为“相思”这两个字李妈妈实在不会用哈语翻译,何况“小鸟”和“相思鸟”发音还挺相似的,而且烟盒上确实有只鸟。
生活里少不了这样的发明创造。不管是黑猫白猫,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李娟家的聪明才智,还在她们家第一次去沙依横布拉克时帮了大忙。
“刚刚下车就对这里不抱信心了。那时,这里一片沼泽,潮湿泥泞,草很深。一家人也没有,只有河对面远远的山坡上驻着两三个毡房。”那年,这里的雨水多得出奇,漏水是常有的事。李娟全家人甚至在半夜去追过被风雨掀掉的帐篷顶。李妈妈很后悔当初为什么不多进一些碗。
在这样的沼泽,这样刮风下雨的夜里,又在广大的牧场中,相邻的毡房之间好像隔了十万八千里。谁还能帮着谁?只能自己靠自己。很快地,他们就想好了办法:用绳子把一只又一只零零碎碎的塑料袋子挂在顶棚下面,哪里漏就对准哪里挂上一只袋子,等那个袋子里的水都接满了,溢出来了,于是又在溢出来的地方再挂一只塑料袋。如此反复,直到把那些水一级一级、一串一串地引到帐篷外面为止。这种方法比哈族老乡的小盒小罐强多了,既不用时刻担心水忘了倒,也不怕踩翻罐子。
别人的颠沛流离往往是出于无奈,为生活奔波。而李娟却在流浪中找到了天堂。在巴尔拉茨,她还偶遇了一段爱情。说“偶遇”是因为才见了八次面就没戏了。
等待总是讨人厌的,可要是等来了那个他,却又是美好的。李娟的那个他——林林,在矿上开白色黄河大卡车。李娟特地学会了辨认汽油车和柴油车的引擎声。因为平均每隔十天,李娟都会等到那辆白色柴油车发出的低吼。跟着林林的黄河车,李娟最记得那一次,林林带她去县里吃大盘鸡。由于超载,黄河车爆了一路的胎,原本八个小时的路硬是走了两天一夜。“到了,到了,大盘鸡快到了……”成了支撑他们走下去的唯一信仰。可为什么幸福总是这么短暂?在迎接完最后一批下山的牧队后,李娟离开了。
“真是奇妙,要是没有爱情的话,在巴尔拉茨所能有的全部期待,该是多么的简单而短暂啊?爱情能延长的,肯定不只是对发生爱情的那个地方的回忆,还应该有存在于那段时间的青春时光,和永不会同样地再来一次的幸福感吧?呃,巴拉尔茨,何止不能忘怀?简直无法离开。”
还有路,在前方等待着李娟,她还要继续漂泊,所以不得不离开。她说过:“妈妈,我只是为了配合你的流浪,才那样瘦小,我为了配合你四处漂泊,才安静无声。”最后的最后,李娟定居了,虽然没有在巴尔拉茨,但还是在她最留恋的阿勒泰。“一个地方令你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那里有你深爱的人和一去不复返的青春吧。”
舒芜说:“《阿勒泰的角落》美在哪里?就美在它明亮的而非阴暗的底色上。寂寞的诗多矣,明亮爽朗下的无边的寂寞似乎还没有人写,这就是独创的境界。”这种寂寞的气息只有精灵才能嗅出。可是精灵只是偶尔途经了喧嚣,她要在走夜路时才能放声歌唱。我们不要多情地去打扰她,她会问我们:“听得到吗?”精灵总会在远离人间烟火的地方,毫无代价地唱着幸福的歌。“但是这首歌很长,我才刚开始。”